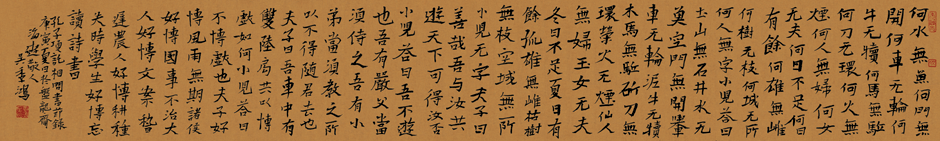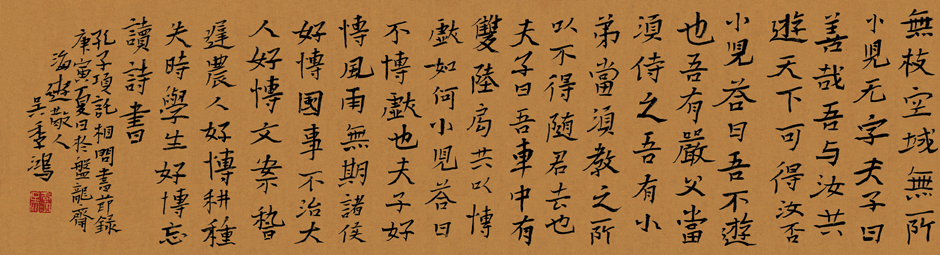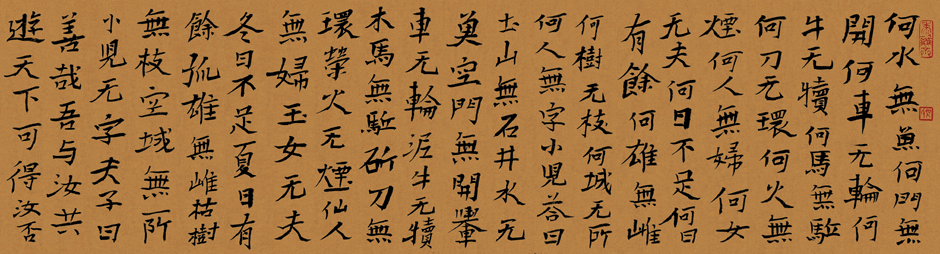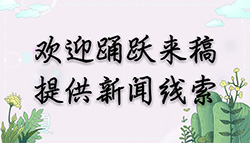吴季鸿,原名继鸿,号海游散人。一九六四年生于浙江台州。先后入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、中国艺术研究院·中国书法院硕士研究生班、中国美术学院首届山水写生创作课题班学习。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、山海墨缘社副社长、台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、台州书画院特聘研究员、三门县书法家协会主席。现任职于浙江省三门县文化馆。
出版有《鸿爪留痕---吴季鸿书法作品集》《搜妙创真---吴季鸿山林之迹》
《峻健其笔 开豁其胸》
我辈跻身书坛而日臻老境之际,忽觉有许多话想说。一方面,为我们这一代有幸亲炙沙孟海、陆维钊等先生而自幸;另一方面,也为我辈中涌起一批领军人物而欣慰。当代书法艺术的繁荣,我们这一代、特别是领军人物们的努力是功不可没的。然而,若能静下心来作客观的审视和主观的自省,又深感惭愧。直到现在,颇具大师潜质和气象的人物鲜见出现;相反,同侪中“江郎才尽”之现象日见迭显。这里既有功力的原因,更有因学养不足而进入审美追求误区的问题。因此,我总感到,在以沙、陆为代表的老辈面前,我们似乎成长不起来。和任何艺术门类一样,书艺总是以某一个时代经典人物的独特贡献来作叙述和评价的,面上热闹只能是过眼烟云。然而,值得欣慰的是,更年轻一代的表现,已可看到超越我们的希望。我想,一方面他们在离开名利场较远的地方,能安下心来面对古人,他们这一代取法魏晋似已成为主流,特别是在我省南部地区,近年来颇见头角峥嵘之士;另一方面,他们比我辈淡定,而无矫情刻意、急于求成之心,大体能以性情的发挥为动力,而未伤及书法本体。而我辈中闯劲较猛者,其创新往往以消解传统为代价,甚至有的不惜“为学神功”而“必先自宫”,迷途难返,甚为可惜。“ 城中桃李愁风雨,春在溪头荠菜花”。
吴季鸿作为台州地区书坛领军人物之一,虽僻处海陬,却视野开阔。他学书既立足浙江,又着眼全国,取法古风,不废今人,志在创新,意存中庸。
在他日省月试的求学过程中,用自己的眼光和思考,积贮了学以致用的主动能量。因此,学古而不泥古,尊师而不盲从,将自己的性情发挥贯穿在学古和创作过程中。由此,他也较早地呈现出自己的书法面貌。
季鸿与大多数同道一样,主攻行草,兼及篆隶,尤以大草见长,书风雄秀跌宕,巧中寓拙。我们知道,中国书法以汉字为艺术化对象,是承载着书家性情和书家生命体征的线条艺术。对于一位寄情大草的书家来说,只有拥有这样品质的线条(其实应该称为笔墨),才能挥洒出如“惊蛇走虺,骤雨狂风”般的意象来。这种令人神往的意象,固然有书家本身的天赋和笔性的原因,更有赖于后天不懈的技艺磨炼和学养充实的努力。
由于大草的表现空间大于今草,因此它不必拘拘于点画形态的精美雅正,而着意于在提按转折运动中对力、势、韵的即兴迹化。因此,在看似抽象的线条组合中,其实蕴含着书家巧妙运用审美辩证关系的功力。对此,当然不能脱离表现力的积累和学养升华两大条件。季鸿早年以颜真卿和米芾为师法对象。除颜楷之外,他特别师法被米芾推为“有篆籀气”的颜书《争座位帖》,形成自己用笔的“顿挫郁屈”。而米芾之书风,被苏东坡喻为“风樯阵马,沉着痛快”,乃得于其万毫齐力的“臣书刷字”。由此可知,颜笔的含忍之力和米笔的飒爽之气的有机融合,赋予季鸿日后的大草用笔以动静、疾涩、欹正、虚实等变化的运动能量。
对季鸿书艺提升具有积极作用的,还有汉隶与魏碑。其中魏碑所具有的野性之美,为季鸿在审美的拓展和笔力的积贮上,增加了新的营养。包世臣在《艺舟双楫》中说:“用笔之法,见于画之两端,而古人雄厚恣肆令人断不可企及者,则在画之中截。盖两端出入操纵之故,尚有迹象可寻,其中截之所以丰而不怯、实而不空者,非骨势洞达,不能幸致。” “画”即笔画,要使线条(笔画)“丰而不怯,实而不空”,若作大草,仅靠“帖学”
一系精于线条两端变化而疏于两端之间过程的充实,在大空间中表现的话,线条只能是“怯”而“空”的,支撑不起表现于大空间的大格局。所以,只能在用笔方法上,追溯魏碑、篆隶,特别是篆书那种按中有提、提中有按、涩笔疾进、万毫齐力的方法,才能解决线条“中截”充实的课题。因此,凡是志在大空间中挥洒的书家,用笔的“取法乎上”,只能如此修炼,才有可能取得更大的表现能力。我想,对此季鸿是有体悟的。
对明贤草书的取法,是季鸿学书的主课,当然更有会心。大草从旭、素开始,一直到明代的解缙、祝允明、徐渭、王铎等,均是以“骤雨狂风”的节奏进行笔墨运动的,季鸿大草的基调亦是如此。然而我也注意到,明代王宠“以拙取巧”(王世贞语)、“”疏拓秀媚”( 邢侗语)的书风也吸引过季鸿的眼光,从而使他的某些作品,在激越的格局中,透露出一缕清和的音韵,难能可贵。
对于一位富有进取心的书家来说,季鸿自然也有创新的冲动,我也看到过他 “返璞归真”的实验性作品。这个现象不是孤立的,不仅现在的中青年,连老一辈中也有志于此道者,如徐生翁先生。沙孟海先生在《题徐生翁杂书小品卷跋》中是这样评说的:“越郡前辈赵撝叔《章安杂说》言,书家最高境,古今二人耳。三岁稚子,能见天质;积学大儒,必具神秀。故书以不学书不能书者最工。生翁晚起,下笔多参小儿体态,殆有昧乎乡先生所云者。世或目生翁主张太过,几欲毁冠裳、披木叶,得失之际,盖难言之。旧时每过绍兴开元寺,欣赏翁三字题榜,峻健开豁,想见早年功力……”高明如沙孟海、陆维钊先生的书艺成就,集中体现在“务追险绝”的领域,却耸起了至今无人可以超越的高峰。他们正是在充分尊重自己性情、尊重适合自己审美理想的前提下,取得卓荦成就的,却并不机械地为求稚子般的“天质”去作“毁冠裳、披木叶”的矫情创新。因此,那种以化解书法的经典游戏规则为手段而“创新”的,只能是哗众于一时,却不能长留于青史。当然,徐生翁先生晚年的变法,有一定的求道愿望,精神可嘉。但正是他这不尽成功的实践,可以使我们不必重蹈前辙。
其实,季鸿对自己的主体书风是很坚持的,正因如此,我建议他不妨把沙老跋语徐生翁《杂书小品》中的“峻健开豁”四字,作为自己持久追求的审美目标,这应该是中国书法艺术古今一致的审美主旋律。
行文至此,忽得佳句,以求共勉:
碑帖并修岁月长,惊诧走虺起苍黄。
当凭情性求新境,荡荡时风任跳踉。
俞建华
庚寅初冬草于庸福斋